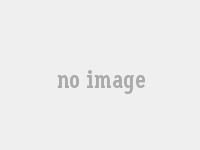虚拟货币交易所项目
自2021年9月24日《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施行以来,为避免红线风险,各大主流虚拟货币交易所纷纷选择清退国内用户。然而,一来部分中小型交易所的主要客户为国内用户,故而选择持续经营;二来刑法评价的是历史行为,清退不意味着已实施的犯罪归为虚无。因此,近半年以来,因经营虚拟货币交易所而延伸各类刑事犯罪层出不穷,本文将以虚拟货币交易所业务模式为标准,分析不同业务模式可能涉嫌的不同罪名,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壹:以人头计酬,吸引客流
区块链应用场景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社群概念的引入,无论是炒币、挖矿、合约,各类经营模式的背后都有社群的影子。某种意义上,官方社群就是平台的宣传与发声渠道。
然而,可能是区块链的各项应用游离在我国法律的灰色地带太久,社群引流的做法往往以人头计酬,形成多级传销结构,涉嫌犯罪。法律对该罪名的描述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及《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我们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分为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以便理解:
1、人数与层级
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包括本数),特别提醒,(1)从下线的下线处取得财物,是三级,不是两级;(2)如曾触犯传销的法律红线,入罪的人数标准会有所降低。
2、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
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一般而言,交易所的经营决策层、各部门负责人以及负责宣传推广的人员难辞其咎。
3、骗取财物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
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宣传者常常对国家法律法规作出错误解读,使得用户误以为自己的投资虚拟货币的行为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同时,夸大虚拟货币价值前景的行为在交易所间接运作的社群中亦是常态。
贰:从事法币交易的业务
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主营业务是虚拟货币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与法币的兑换。兑换业务通常以C2C的渠道完成,即卖方挂单后,由买方购入。在这一过程中,为保障交易的安全性,交易所通常会通过中心化的钱包地址或其他途径经手用户的虚拟货币并为用户提供虚拟货币及法币的支付结算。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第三项以及《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虚拟货币交易所提供法币交易服务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一般而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交易所的经营管理层及对资金流向较为了解的员工将均涉嫌非法经营罪。
我们要指出两种应当除外或者说至少值得商榷的出罪情形:
其一,平台完全不经手法币与虚拟货币,未形成可控制的“资金池”,未向用户提供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其二,平台没有法币交易,仅有虚拟货币之间的交易。将虚拟货币解释为资金有类推解释之嫌,笔者持反对意见。
叁、从事类期货的合约业务
合约玩法是虚拟货币交易所业务的重中之重,简单来说,就是约好在某个时间按照特定价格交易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通常交易所会效仿期货提供标准化的合约,以没有明确交割日的永续合约为主。
从司法机关的视角来看,类期货的合约业务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红线风险:
第一,虚拟货币交易所未经过我国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从事期货衍生品交易,该合约产品可能因此被认定为“非法期货”。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前半部分所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模式。即,合约业务可能与非法经营罪相关联。在2022年4月20日发布的《期货和衍生品法》(尚未生效)与去年发布的《期货法》草案中,期货衍生品已被监管纳入视野,相较于过去对期货狭隘的解释空间,新的法律已经赋予了期货解释上的其他可能,合约业务被作为“非法期货”予以规制的可能性亦因此提升。
第二,根据《辞海》的解释,赌是指用财物作注比输赢,赌博的目的是财物上的输赢,因此赌博是指以偶然的事实决定输赢而博取财物。合约标的虚拟货币的涨跌本身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用户购买合约的行为在司法机关的视野中至少能够以赌博定性,而为用户提供购买合约之场所并从中抽利的行为自然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紧密相关。相较于动辄15年以上或无期的其他罪名量刑,十年封顶的开设赌场罪已然属于经营虚拟货币交易所的轻罪。
合约的延伸:设置技术后门,“插针”爆仓
因虚拟货币不存在涨停、跌停的说法,为避免用户过度亏损,合约通常存在“自动割肉”的爆仓设计。部分虚拟货币交易所因自身下场买合约、用户爆仓可抽利等原因,会以占有用户合约投资为目的故意设置技术后门,使得特定虚拟货币的价格脱离市场的实际情况,并通过控制涨跌令购买合约的用户爆仓,并最终让价格波动的图示变成“针”状。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基于对交易所展示的虚假价格波动图示的错误认知,处分了自己作为财产性利益的虚拟货币。上述虚拟货币交易所以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意思占据了用户虚拟货币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需要指出,“插针”在自然的市场波动规律中亦会产生,不能以“插针”的出现作为交易所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但如若币价与主流交易所存在偏差、频繁出现“插针”且大量用户因此而爆仓的,该虚拟货币交易所涉嫌诈骗罪的可能性便大幅度提高了。
肆、提供币本位的理财服务
部分虚拟货币交易所会提供币本位的理财服务,理财的资本运作渠道包括但不限于云挖矿、交易所搬砖、代为投资合约等。在交易所的界面上,通常会显示币本位的理财收益率等信息。
这一业务模式的非法性体现在虚拟货币交易所不为我国监管体系所承认,交易所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提供理财服务的金融机构资质。基于此,笔者以为,理财服务存在两项红线风险:
其一,《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正如其名,该罪名的行为特征表现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交易所提供的理财、借贷等服务属于金融机构特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可能被解释进实质性的“擅自设立”的范畴。
其二,《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二罪名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体表现为吸收资金的用途,客观上的“非法吸收资金”体现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吸收社会公众资金做资本运作的行为。虚拟货币交易所的理财服务符合“非法吸收资金”的构成要件,涉嫌上述二罪名。
当然,币本位的理财不能等同于法币理财,该业务存在的刑法风险存在一定的辩护空间。虽然实务中有将虚拟货币纳入资金范畴的生效判决,但笔者对此仍持反对意见:将虚拟货币解释为资金属于类推解释,不利于公民对刑法红线的把握,亦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All last
虚拟货币交易所在国内的经营虽受到了否定性的法律评价,但世界范围内数字资产去中心化的发展、WEB3.0的发展却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除特别恶性的诈骗、传销做法之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业务危害性恐怕并不在于对民众财产利益的侵害,而是在于其对我国监管规则与思路的违背。交易所的经营者希望拥抱监管,但监管却以一刀切的做法拒绝金融创新业务的规范化——这样的情形在各领域内不断重复发生。笔者只希望,审判机关在对该类案件定罪量刑之时,冷静考虑一下这些创新行为与传统犯罪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是否一致,为市场保留一些热忱与信心。